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建立教授(左)在開展冶金考古教學和科研工作。海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創建了系統完整的蝶變大咖中國考古學科教研體系,被譽為“中國考古學家的人民日報搖籃”;在田野考古學、考古年代學等研究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海外圖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何嘉寧教授團隊開展研究。版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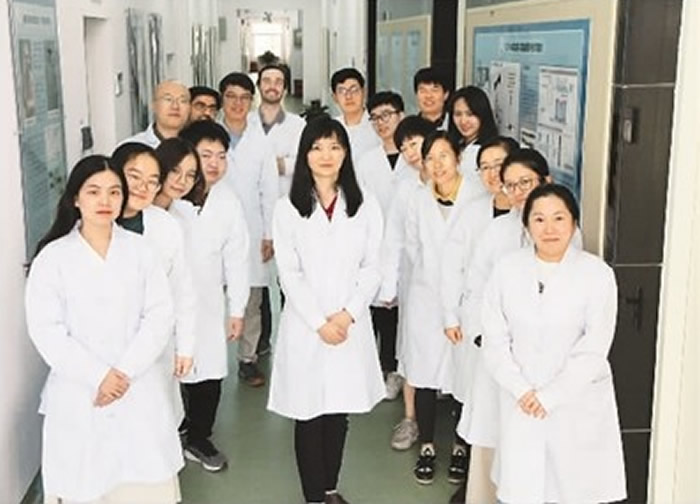
中科院古脊椎所是我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考古學的開拓者和核心研究力量。由付巧妹研究員(中)領導的人民日報具國際頂尖水平的分子古生物學實驗室和研究團隊,在生命科學與地球科學的海外交叉前沿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在國際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的研究成果。
(神秘的版共地球uux.cn報道)據《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 王美華):打造科技考古“朋友圈”“工作群”
“這是考古行業的一件大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簽訂和聘請儀式上表示:科技考古在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和學科建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此次戰略合作的未來目標,是建立國家考古實驗室。
共建這3個實驗室,獨特作用在哪?“有利于優勢互補!”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中心主任唐煒介紹,考古中心在行業資源、行業調度方面有獨特優勢,而青藏高原所、長沙開福本地小姐(上門服務)本地小姐vx《189=4143》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古脊椎所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都是行業最頂尖、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考古科研機構,在科研力量、技術水平、人才隊伍儲備上具有極大優勢。此次共建聯合實驗室,實際上是把行業資源和頂尖技術結合起來,把研究對象交給最專業的團隊,助推考古工作的發展。
“同時,也有利于加強統籌規劃,解決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兩張皮’現象。”唐煒表示,開展考古事業發展規劃研究,從整體上加強統籌規劃,有利于增強考古工作的系統性,推進多學科、跨領域、高水平的考古學研究。“雖然大部分田野考古工作者已經意識到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但在實際工作中,很多人對科技考古的認識還不到位,只是把它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唐煒指出,科技考古應該是一種理念、方法,“如果一開始沒有把科技考古考慮進去,明確用哪些科技手段解決哪些問題,在考古工作后期或結束后再考慮,很多重要信息就已經喪失了,我們都知道——考古資源是不可再生的,考古工作沒有后悔藥可吃”。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承擔分析監測技術、空間及微觀測量技術、新材料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等技術考古科研,考古標準技術規范研究,組織水下考古、邊疆考古、科技考古、中外合作考古等工作。唐煒表示,考古中心將致力于聯合國內科技考古各領域的優勢單位,以共建共享方式,打造科技考古的“朋友圈”和“工作群”,集中多方優勢資源,加強實驗室建設,牽頭承擔重大考古項目中的科技考古任務。
“科技考古是考古中心的新職能,也是優先發展的重點方向。”唐煒這樣判斷。
“國家隊做國家事,盡國家責”
“青藏高原所作為‘國家隊’,我們作為國家人,要做國家事,盡國家責。”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長陳發虎擔任了“環境考古實驗室”主任,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工作意義。環境考古是作為人文學科的考古學與自然科學交叉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向,青藏高原所擁有完善的實驗和觀測平臺,可以利用多種載體定量重建人類的生存環境,也可以對動植物大化石和微體化石進行分析。“目前我們正在大力發展利用生物標志物、古環境DNA、古蛋白等新興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手段進行古環境重建方面的研究。”環境考古實驗室執行副主任、青藏高原所楊曉燕研究員表示,聯合實驗室將聚焦東亞及周邊地區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及其與生存環境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聚焦青藏高原地區人類對極端環境的適應過程、高寒文明產生和發展過程。
“目前在國際上,通過古DNA研究東亞人類的起源與演化,尤其是我們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研究是非常匱乏、相對空白的。”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長鄧濤研究員表示,共建分子古生物學實驗室,就是希望用最前沿的分子古生物學方法,在揭示早期現代人在中國起源與演化的規律,復原中國乃至東亞不同時期現代人的遷徙路徑、行為方式和生存面貌,厘清其與古老型人類的遺傳關系和互動過程等這些關鍵的、亟待探索的科學問題上取得重要突破,為更新世晚期以來中國境內人類的演化提供更為翔實的證據,繪制出宏大且細致的東亞人群遺傳歷史圖景,發展或提出更準確的人類演化理論。鄧濤研究員說:“在中國人類史前文明的發展方面,我們將通過跨學科合作、最新科學技術的應用,在農業的起源、中國境內各種史前文明和相關人群的發展脈絡等方面進行探索,希望能在中華文明探源領域有重大的突破。”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動植物考古學以及文物材料學分析等方面處于國內領先地位,其考古年代學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年代與動植物考古聯合實驗室成立后,擬開展的重要課題和重點遺址包括夏文化年代研究、三星堆祭祀坑科技考古研究、‘南海一號’沉船全面科技考古研究等。”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崔劍鋒介紹,雙方將共同完成考古遺址絕對年代研究、出土動植物遺存鑒定和分析、出土器物殘留物分析、食譜分析、文物材質、成分和同位素分析等工作。通過深入合作,運用前沿科技手段充分發掘中國考古遺址與文物資源的研究價值與歷史意義,力爭取得重大突破和創新發展。
前沿科技“讓考古遺存開口說話”
“考古學意味著‘一眼千年、萬年、百萬年’,是考古人通過物質遺存研究逝去歷史的學問。”分子古生物學實驗室主任的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員表示,考古遺存本身不能說話,但通過現代各種科技手段可以充分發掘出豐富、多樣化的歷史信息,為我們更全面地揭示過去歷史的面貌提供各種維度的幫助,因此考古學從創始就是科技的。付巧妹介紹,當前,在影像學、年代學、基因組學、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各種新興前沿學科的滲透下,科技考古通過跨學科的融合和現代各種科學技術的運用,迸發出新的活力。
“進入21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考古學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年代學與動植物考古實驗室主任、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吳小紅教授表示,現如今的考古學研究基本上都是考古學主導下的多學科聯合研究。
“比如良渚遺址發掘過程中,涉及了碳14年代學、動植物考古學、地質考古學、分析化學、文物保護等十幾個學科數十名專家團隊。”崔劍鋒介紹,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年代學、動植物考古學研究、玉器產地研究等方面給予了大力協助。這種多學科介入、科技信息的全面提取,為良渚遺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提供了堅實的科學證據。
“青藏高原所在考古工作中應用的科技手段,包括人類生存環境,包括溫度、降水的定量重建,以及遺址出土動植物遺存鑒定和分析等。”楊曉燕介紹,他們曾利用植物大遺存分析揭示了青藏高原腹地的生業經濟,并發現東西方農業的傳播與交流幫助人類克服不利的氣候變化而向高原擴散和定居。“如今環境考古的新階段是運用新的技術手段,獲得更多的古人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信息,在生態系統的角度下,探討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我們的重大考古項目,尤其近年來運用分子古生物手段展開的科考項目,都需要多機構、多學科共同參與合作,廣涉考古學、古人類學、遺傳學、生物信息學等多學科領域。”付巧妹介紹,早在百年考古大發現——“北京人的發現”重大考古項目,發掘出的第一個完整的遠古人類的頭蓋骨化石,就是集合了多家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的結果。“2020年,古脊椎所與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多家考古單位和科研院校合作,首次開展大規模、系統性的南北方史前人類基因組的研究。”付巧妹介紹,通過對大量史前人類樣本材料進行古基因組實驗和數據分析,了解到近萬年來中國人群的南北分化格局和不斷遷徙、混合的歷史,在考古學領域長期以來富有爭議的南島語系人群起源的問題上起到重要助力。有國外媒體報道,該研究修正了此前流行的、基于頭骨形態學提出的有關東亞與東南亞祖先人群的“兩層假說”,填補了人類演化史所缺失的重要中國篇章。(本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鏈接3個聯合考古實驗室成立
2021年2月1日,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考古中心”)分別與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簡稱“青藏高原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考古中心分別與青藏高原所、古脊椎所、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共建“環境考古實驗室”“分子古生物學實驗室”“年代學與動植物考古實驗室”,聘請中科學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長陳發虎,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員,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吳小紅教授擔任實驗室主任。聯合實驗室的成立將推進多學科、跨領域、高水平的考古研究。 頂: 7踩: 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