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東菊在考古發掘中

白石崖溶洞

張東菊在青海湖的項發現山學校發掘工地附近,她說風景美極了。東大東菊
(神秘的友張地球uux.cn報道)據齊魯晚報(記者 馬純瀟):7月15日,第十七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頒獎典禮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隆重舉行。獲獎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2000級校友、青藏前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張東菊獲獎,高原古人這是類因這位近年來多次登上世界學術高峰的女考古學家獲得的又一項殊榮。
張東菊是項發現山學校誰?她都取得了哪些成就?近日,她在緊張的東大東菊考古發掘工作之余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讓我們一起走近這位與濟南有緣的友張奇女子,了解一下蜚聲世界的獲獎女考古學家是如何煉成的。
她在高原
青藏高原成就了張東菊。青藏前她的學術成就,源于“她”和“她”在青藏高原的一場跨越16萬年的相遇。
第一個她,是張東菊,現蘭州大學環境資源學院教授;第二個她,是16萬年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人類,被張東菊團隊命名為“夏河丹尼索瓦人”,簡稱“夏河人”。
從2010年起,張東菊闖入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競賽,“她”便開始了對“她”的苦苦尋覓。
這場學術競賽要從2008年說起。當年,俄羅斯考古工作者在西伯利亞南部阿爾泰山脈的丹尼索瓦洞發現了一個全新的屬于古老型智人的人類種群,命名為“丹尼索瓦人”。由此,揭開了一場世界范圍內學術競賽的序幕,尋找和研究丹尼索瓦人成為世界學術界的熱點
丹尼索瓦人的研究為什么能成為世界學術熱點?因為它對于我們理解和認識人類演化歷史,特別是現代人起源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丹尼索瓦人被發現之后,科學家把他們的基因與現代人類的基因進行對比。結果發現,在大洋洲某些群體中約有5%的基因貢獻,在東亞、南亞及美洲部分群體中約有0.2%的基因貢獻, 而對非洲、歐洲和中亞部分區域的現代人則無基因貢獻。這些發現和研究,對于我們解決“我是誰我來自哪里”這一古老命題,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張東菊于2010年在蘭州大學博士畢業,當時她的導師陳發虎院士將一塊人類下頜骨化石交給她研究。這塊化石是上世紀80年代在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的白石崖溶洞發現的,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對其開展研究,然而這塊被擱置了很長時間的化石在張東菊手中卻有了驚人的發現。她的團隊通過古蛋白的分析,發現這塊化石的種群屬于丹尼索瓦人,其年代為距今至少16萬年!她們將其命名為“夏河丹尼索瓦人”。研究成果于2019年在世界頂尖雜志《自然》發表,立即引發了世界學術界的轟動。之后,科學家又根據相關DNA信息和那塊下頜骨化石復原了夏河人的頭像。
在研究化石的同時,張東菊團隊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兩次對白石崖溶洞進行考古發掘,并成功在遺址沉積物中提取到丹尼索瓦人的DNA.,她們新的成果于2020年登上了另一世界頂尖雜志——《科學》。
張東菊說,當初在白石崖溶洞發掘時,她曾經無數次幻想過,這些古人類是誰?他們是何時生活在這里?他們又是如何在對現代人都充滿挑戰的青藏高原長期生活的?現在,她和他的團隊已經回答了前兩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他們正在尋找答案。
“山高人為峰”。在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張東菊取得了一些令人炫目的上海靜安同城(上門服務)vx《189-4143》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成績。她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曾入選“2019年度十大科學突破”、“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發現”、“2019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新聞”等。
“命中注定”干考古
一系列的成績表明,張東菊在她的學術領域已經登上了頂峰。那么,她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呢?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命中注定”。
張東菊參加高考是在2000年。在填報志愿時,她偶然看到山東大學有考古學專業,當時她并不太了解考古學具體是干什么的,感覺可能跟小時候看的《聊齋志異》里面挖寶的情節有關。她從小好奇心比較重,對她來說寶貝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覺得挖寶的過程特別有意思,所以當時就想填報考古學。
那年山大考古系只在她所在的河北省招兩個學生,競爭還是挺激烈的。加上她上中學時特別喜歡英語,也想將來學英語,所以報志愿時她把山大報為第一志愿,第一個專業則是英語,想把考古學放到第二志愿。
但是,這時候二舅出面了。“二舅”現在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張東菊的二舅也不簡單,是她家族里學歷最高最有見識的人,對她來說也是影響很大的。在咨詢二舅如何報志愿時,二舅說,考古學是冷門,將來不好就業,還是不要報了。當時的張東菊對就業完全沒概念,但是還是聽了二舅的話,把專業換成了其他稍微熱一些的專業,比如國際貿易。
錄取結果是張東菊通過打電話得知的,當聽到被錄取到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她填報志愿時選擇了服從調劑)時,她激動壞了,這就是之前想報考的專業呀,“你說我學考古干考古不是命中注定嘛!”若干年后,張東菊一直這么說。
張東菊在濟南開始了她的大學生活。濟南是張東菊從小去過的第二個大城市,四年的大學生活中,趵突泉、大明湖都留下了她的足跡,印象深刻的還有經常閱讀的《齊魯晚報》 。當然,讓她最難忘的還是在山大考古專業四年的學習。
“能進入山大學習,我真的覺得特別幸運。學校的學習氛圍很濃厚,文史樓很有歷史氣息,老師們都很博學。”張東菊說,當年給他上課的欒豐實老師、于海廣老師、方輝老師、任相宏老師、王青老師等都會在課堂上列出一些參考文獻,她經常去圖書館查閱這些文獻,雖然那時對這些專業文章看不太懂,但是感覺自己接觸到了第一手資料,感覺特別難得,會硬著頭皮讀下去。她還記得上《考古學通論》時,欒豐實老師曾經提著兩副人骨架標本進教室,讓同學們認人骨,有些同學嚇得花容失色,而她竟然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我真的就該學考古”。
張東菊回憶說,山大考古在她讀書時應該是在國際合作方面做的最好的一家。當時方輝老師(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與美國學者做的兩城鎮調查名氣很大,成果也很顯著。雖然她那時只是本科生,沒有參加過調查,但是每次合作的國外學者過來都會給他們做講座,這讓她感覺受益匪淺。那時候方老師親自出任翻譯,那口流利的英語把同學們都驚呆了。這些國內國外學者的報告與交流,大大拓寬了他們的學術視野,為她后來從事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張東菊在她之后的學術生涯中,也特別重視國際交流與跨學科的合作。
張東菊說,山大讓她親身體驗了什么是大學,給她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也開闊了她的視野,不光是學術的,更是人生的。
成功需要運氣更需要堅持
從山東大學本科畢業后,張東菊進入蘭州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師從陳發虎院士。那么,張東菊的學術人生從此就一路開掛了嗎?其實并非如此。
“不管在我上學時,還是工作后,其實都不是一帆風順。一段時期內我的工作進度非常慢,許多年都沒有研究成果,那時候內心是很惶恐的,甚至有時候會絕望。幸運的是,我的導師陳發虎院士一直耐心細致地給我指導和鼓勵,他從來都沒想放棄我。盡管他工作很忙,但總是不厭其煩地督促我、鼓勵我。”
對于后來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張東菊覺得一是運氣好,更重要的則是堅持。
說到運氣,張東菊講到了自己的名字。別人一看“東菊”很容易想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句詩,認為名字起得很有詩意。“其實這名字是我姥姥起的,姥姥并沒有文化,也不知道這句詩,因為我姐姐叫東雪(后來改為了冬雪),而姥姥的村里正好有個叫東菊的,特別有福氣,姥姥就覺得這個名字好,希望我也有福氣,給我父母建議給我取名叫東菊。”
張東菊說,如姥姥所愿,她感覺自己確實很有福氣,運氣非常好。要說國內很多學者成就也很大,但是由于所研究領域不同,很難獲得世界范圍內更大的認可。“如果你研究唐宋的話,確實很難在國際上產生大的影響。我研究的時代比較早,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競賽,所以動靜相對會大一些”。
當然,運氣之外,堅持的意義更大。張東菊說,“一路走來,遇到過許多困難和挫折,有很多次實在扛不住、頂不住,差一點點兒就放棄了,然而放棄又不甘心,我就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再堅持一下,最后終于挺過來了。曾經過如果哪一次真的放棄了,也就沒有以后了”。
女考古學家的苦與樂
堅持,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眾所周知,考古很艱苦,女考古學家更艱苦,在高原工作的女考古學家尤其艱苦。但是對于一個成功的女考古學家來說,她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她能在苦中發現和得到樂趣。
對于普通人來說,來到高海拔地區一般都會有高原反應,張東菊也有。她來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區時,會頭沉甚至頭疼,睡覺不踏實,走路只能慢慢走。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經常要蹲下撿石器再站起來,“這時候蹲下起來的動作一定要慢,否則會頭疼。”張東菊戲稱在高海拔地區跑調查是“高原漫步”,像在做各種慢動作。
對于考古學家來說,高原反應雖然帶來痛苦,卻也能帶來靈感。“你知道青藏高原的居民為什么沒有高原反應嗎?是因為他們體內有EPAS1變異基因。”張東菊說,當初在俄羅斯發現丹尼索瓦人時,科學家在他們的DNA中檢測到了EPAS1變異基因。專家們就感到非常難以理解,丹尼索瓦洞所在的海拔只有700米,丹尼索瓦人身上怎么會有這種基因呢?“當我們在青藏高原發現了丹尼索瓦人之后,這一疑問不就迎刃而解了嗎?”
這就是考古帶來的思辨之美。
近幾年張東菊開展考古發掘的白石崖溶洞和青海湖都是海拔3300米左右,海拔不算太高,她在這兩個區域都沒有高原反應,但是這里紫外線特別強,早晚溫差大,就算夏季出來做發掘,也要帶上沖鋒衣甚至羽絨服,因為一下雨就會特別冷。
2018年張東菊在白石崖溶洞搞發掘是在冬天的晚上,“氣溫零下十幾度,一旦刮風便感覺如刀割一般”,張東菊說。她們經常穿著厚厚的衣服去洞里發掘,但來到洞里卻是又一番景象,這里溫暖如春。“我們真的要感嘆十幾萬年之前的人類太會找地方了。”當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從若干沉積物中提取出丹尼索瓦人的DNA后,那快樂真的難以言表。
這就是考古帶來的發現之美。
女考古學家也是女性,當然也愛美,在合適的環境下也想穿漂亮的裙子。但是當張東菊感受到考古帶給她的更強烈的美的愉悅之后,平時就對著裝打扮不太在意的張東菊似乎并不太在意考古讓她損失的“愛美的權利”。
在她看來,她所在的考古工地就是最美的。“現在我正在青海湖做考古發掘,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湖,非常漂亮,因為太陽、云、風和水的變化,這里的景色每天都不一樣,美輪美奐,每天都可以看不一樣的落日和晚霞,還有美麗的大草原,各種野花相繼開放,讓人心曠神怡。每天收工吃完晚飯,我會在草原上散步,現在我已經認識了這里大部分的植物,還時不時會看到小鳥的鳥窩,下雨后還可以采采蘑菇……”
比賽繼續
美麗的風景,愜意的生活,張東菊敘述得很詩意。可是無論怎么詩意,其實質就是說,她的發掘工作又開始了。
她們的發掘工作一直在持續。張東菊說,自己不敢有半點松懈。“丹尼索瓦人研究是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也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白石崖溶洞是目前全球確定出土丹尼索瓦人遺存的僅有的兩處遺址之一,非常重要。作為這個遺址的主要研究人員,我有責任保證這個研究遺址的研究有國際最先進的團隊、利用最先進的技術、采用最完備的研究方案來進行。”
張東菊的頭腦中還有一個接一個的疑問:丹尼索瓦人在青藏高原上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他們與現代智人是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必須靠發掘和研究來尋找答案。張東菊知道,關注丹尼索瓦人研究的有許多學者和團隊,遍布全世界。那么,誰又將在接下來的競爭中獲得領先?
比賽仍在繼續,讓我們為張東菊加油!(本文配圖均為受訪者提供)
相關報道:青藏高原16萬年前古人類如何被發現?考古學家揭秘“夏河人”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齊魯晚報(記者 馬純瀟):“是誰帶來遠古的呼喚……”,每當聽到她們唱起這首《青藏高原》,那蕩氣回腸的追問便會直抵靈魂深處。然而多少年來,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直到一位名叫張東菊的女考古學家用她震驚世界的發現告訴我們,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呼喚,來自距今至少16萬年前的“夏河丹尼索瓦人”(以下簡稱“夏河人”)。
這一發現,為張東菊贏得多項世界級榮譽,近日,她又因此榮獲“第十七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
那么,“夏河人”究竟是什么人?“夏河人”是如何被發現的?他們與現代人類是什么樣的關系?又有哪些已解和未解之謎?這一切,需要從“X女孩”講起。
X女孩
2008年,俄羅斯考古工作者在西伯利亞南部阿爾泰山脈的丹尼索瓦洞發現一小段人類指骨化石,一同發現的還有一些石器。
科學家通過對指骨化石提取的DNA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指骨的主人是一名5到7歲的小女孩,被昵稱為“X女孩”。“ X女孩”并不屬于我們此前已知的任何一個人類種群,既不同于現代智人,也不同于此前已知的尼安德特人,而是屬于生活在幾萬年前的一支此前未知的古老型智人,被命名為“丹尼索瓦人”,其年代大約在距今7.6-5.1萬年。
丹尼索瓦人的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震動,該研究被《科學》雜志(Science)評為2012年度十大科學突破之一。
丹尼索瓦人的發現為什么如此轟動?因為它對于研究人類演化和現代人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關于現代人起源的研究已經顛覆了許多我們原來的認知。比如,我們小時候課本上說,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如藍田人、北京人,是我們的祖先。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很有可能不是我們的祖先或者直系祖先。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我們的祖先是從非洲走出來的早期現代人,他們在走出非洲的過程中取代了當地的土著人群,如藍田人和北京人的后裔。那么,我們的祖先在走出非洲以后,與遇到的非洲以外即歐亞大陸的古老型人類是什么關系呢?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基因交流嗎?
丹尼索瓦人被發現之后,科學家把他們的基因與現生人群的基因進行對比。結果發現,丹尼索瓦人對大洋洲的某些人群有約5%的基因貢獻,對東亞、南亞及美洲的部分人群有約0.2%的基因貢獻,而對現代非洲、歐洲和中亞人群沒有任何基因貢獻。這些發現和研究,對于我們回答“我是誰,我來自哪里”這一古老命題,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一項重大發現通常會伴隨著眾多的不解之謎。比如,科學家檢測到了丹尼索瓦人的DNA中含有一種特有的EPAS1變異型基因。在此前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這種變異型基因是人類適應高海拔環境的關鍵基因之一。我國長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居民一般都有這種基因,這使得他們不像外地人到達海拔較高的地區會產生高原反應。可是,丹尼索瓦洞所在的地區海拔只有700米,丹尼索瓦人身上怎么會有這種高海拔適應基因呢?他們是從哪里來呢?由于丹尼索瓦洞最先發現的只有一小段手指骨化石,雖然隨后又報道了幾件牙齒或牙齒斷塊,但學者們仍然無法據此復原丹尼索瓦人的形象。那么,他們究竟又長什么樣呢?
從此之后,關于丹尼索瓦人的發現與研究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熱點,而張東菊幸運地闖進了這個新的世界學術競賽場。
一塊古老的化石
丹尼索瓦人的發現改寫了人們對人類演化歷史的認識。既然基因檢測發現,丹尼索瓦人對東亞、東南亞、大洋洲等地的現代人類有一定的基因貢獻,這說明丹尼索瓦人在滅絕之前與現代人類是有基因交流的,并且基因交流事件最可能發生在這些區域。因此,科學家們推斷,過去的幾十萬年間,這個古老人群曾遍布歐亞大陸東部,在這期間與早期現代人有過頻繁的接觸。盡管如此,在此區域除丹尼索瓦洞外,考古學家卻一直未找到丹尼索瓦人的化石證據,而張東菊及其團隊幸運地成為破局者。
這要從一塊古老而又富于傳奇色彩的化石說起。
上世紀80年代,在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的白石崖溶洞,一位僧人偶然撿到了一塊奇特的化石,化石形狀顯示可能是人類下頜骨,上面還有兩顆牙齒,但這塊下頜骨又比我們現代人的下頜骨大的多。僧人感覺這肯定是好東西,便將它交給了自己非常尊敬的六世貢唐活佛。
貢唐活佛看見了這塊奇特的化石,也覺得這個東西不簡單。他從上世紀80年代起,便與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員、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兼職教授董光榮有交往。知道董光榮在從事內蒙古的薩拉烏蘇遺址和“鄂爾多斯人”研究,并經常和化石打交道,活佛便將僧人送來的重似石頭的骨頭交給了他,希望對他的研究有所幫助。
董光榮把化石的事情告訴了蘭州大學的環境考古團隊的帶頭人陳發虎院士,希望能一起研究。但是由于二人的研究重點都在環境考古,所以對這塊化石的研究并沒有顧上。直到2010年張東菊博士畢業留校工作,作為陳發虎院士團隊的主要成員之一,她開始對化石進行真正的深入研究。
張東菊,現任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她本科畢業于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保送到蘭州大學跟隨陳發虎院士攻讀環境考古方向的研究生,碩士和博士期間主要從事的舊石器時代環境考古研究。化石能交到張東菊的手中,對于她來說當然有幸運的成分,但這其實更多的得益于她的學術背景,由她來研究這件化石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這是一枚長約12厘米、整體呈土黃色的人類右側下頜骨化石,這塊化石僅保存了古人類下頜骨的右側,下頜骨附著第一臼齒和第二臼齒,其他的牙齒僅保留牙根部分,頜骨形態粗壯原始,臼齒較大。在沒有測量的情況下,研究人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是沒有下巴的,首先說明它不是現代人化石。
對于化石的研究,張東菊首先想到的是對化石進行古DNA分析。遺憾的是,研究人員發現,該化石并未保存古DNA信息。張東菊說,在生物死亡過程中,細胞會逐漸發生自溶,隨著大量蛋白酶、DNA酶等的釋放,DNA很快會被降解。
既然找不到DNA,研究團隊便將目光轉向了古蛋白分析。蛋白質比DNA“幸存”的時間要長,它們的化學和分子組成更穩定,分解速度沒有那么快。而構成蛋白質的氨基酸化學結構最終由生物體DNA中特異的編碼序列所決定,因此,通過比較不同物種中相同蛋白的氨基酸組成,可以認識物種之間親緣關系的遠近。
古蛋白質分析結果最終令張東菊和整個研究團隊人員欣喜若狂。研究發現,該化石古蛋白中反映的遺傳信息與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親緣關系最近,由此可以確定,該化石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研究人員命名為“夏河丹尼索瓦人”。研究人員還通過測量化石碳酸鹽包裹體沉積的年代,確認該化石形成于距今至少16萬年前。
2019年,張東菊團隊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的Nature(自然)雜志上發表:這是至少16萬年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的化石!之后,基于這件化石和此前已知丹尼索瓦人的DNA信息,研究人員畫出了第一幅丹尼索瓦人的頭像。
這距離丹尼索瓦人的發現已經過去了七年多時間,當全世界的科學家在世界各地苦苦尋找下一個丹尼索瓦人的線索時,張東菊及其團隊的成果立刻在國際國內古人類學界和考古學界引起巨大轟動,得到了國內外同行專家的廣泛肯定和支持,并入選教育部“2019年中國高等學校十大科技進展”、科技部“2019年中國科學十大進展”、Science雜志評選的“2019年度十大科學突破”、Archaeology雜志評選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發現”、Science News雜志評選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新聞”等。
深夜的發掘
榮譽紛至沓來,質疑也隨之而至。由于化石發現時間較早,具體出土層位信息缺失,仍有部分學者對于環境考古團隊歷經近十年的調查以及研究結果懷有質疑:白石崖溶洞是否為化石的出土地點?古蛋白質分析顯示下頜骨屬于丹尼索瓦人這一結果是否可靠?
其實,田野考古出身的張東菊更知道這塊化石固有的“缺陷”:這并非考古發掘所得,沒有明確的出土地點更沒有明確的地層關系。要彌補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因此,伴隨著對化石的研究,張東菊及其團隊從2010年就開始了田野調查。他們團隊用了六七年時間,以白石崖溶洞所在的甘加盆地為中心,逐一考察了方圓6000平方公里范圍內的大小二十幾個山洞,試圖找到更多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以及夏河人在白石崖溶洞生活的證據。
而連續六七年,團隊成員每年都只能以游客的身份去白石崖溶洞考察,“只能看,不能挖,不能采集。”為什么呢?咱們前面曾經說過,那塊夏河人化石最初是由一名僧人撿到。而之所以被僧人撿到,是因為白石崖溶洞原本是個佛教場所,現在由當地的白石崖寺管理,平時也有許多僧人和信徒在此修行、朝拜。此外,這個溶洞也是夏河縣有名的旅游景點,尤其夏季,游客眾多。因此為了不影響當地僧眾和群眾的佛事活動,以及游客的參觀,張東菊及其團隊的考察活動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很難有大的收獲。
轉機發生在2016年。張東菊等再次“游覽”白石崖溶洞時,偶然間在洞口通道處發現了一處并未覆蓋堅硬鈣板的松散土狀堆積,在群眾踏開的堆積物中,張東菊發現了幾塊石頭,仔細辨認,驚喜地發現竟然是打制石器!
他們據此確認,白石崖溶洞遺址保存有史前考古遺存!
研究團隊向國家文物局提交了考古發掘申請,歷經兩年之后終于獲批。2018年12月上旬,蘭州大學環境考古團隊首次正式進洞進行考古發掘。
他們的發掘時間很特別——冬天的晚上。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段,是因為擬定發掘區域位于洞穴較為狹窄的入口通道區域,而一年之中,只有這個時段溶洞里佛事活動少,游客也少,發掘活動才能夠正常進行,而也不會影響到僧眾和游客的活動。
近二十天時間里,張東菊帶領著研究生們一起發掘洞穴,每晚七八點進洞、清晨收工。雖然辛苦,但是收獲頗豐。“我們挖到了1.6米深,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動物骨骼。”張東菊介紹。
之后,蘭州大學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于2019年再次對白石崖洞遺址進行正式考古發掘,兩次共發掘T1~T5五個探方, 總發掘面積為11 平方米。其中, T1~T4探方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動物骨骼,已發掘地層可分為11層(未見底),每一層位均有石制品和動物骨骼出土,底部第10層和第11層尤為豐富,反映了該洞穴曾被史前人類長期占據。
兩大重要成果
上面的說法專業而且籠統,你可能還難以明白張東菊和她的團隊到底收獲了什么。概括來說,她們的主要成就一是在白石崖溶洞獲得了丹尼索瓦人的古DNA,同時獲得了豐富的史前人類活動遺存(石器和動物骨骼等),二是利用白石崖溶洞的出土樣本獲得了可靠的測年數據。
對張東菊來說,通過發掘獲得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和DNA應該她最想得到的結果,獲取DNA最直接的方式是找到化石。然而,化石的形成和發現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在近些年科技的發展,讓他們有了另外獲取DNA的方法,那就是沉積物古DNA分析。
“動物或人死亡之后,線粒體中的遺傳物質——線粒體DNA也會降解,斷成一段一段,它能否經過數萬年的歷史演變保存下來,則與保存環境密切相關,一般來說越干越冷的地方越有可能保存。”張東菊介紹,沉積物古DNA分析是一種新興的DNA分析技術,可以獲得曾在遺址活動的古人群信息,彌補人類化石可遇不可求的缺憾。
古DNA的提取是跨領域多學科協作的結果,與張東菊合作的是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付巧妹團隊。既巧合又令人艷羨的是,不久前付巧妹和張東菊雙雙獲得“第十七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
遺址發掘前,張東菊與付巧妹一起制定采樣計劃,考古人員身穿防護服把沉積物古DNA樣本提取到無菌袋里,最大限度地減少接觸和污染。就像用吸鐵石把一堆混雜的金屬中的鐵塊吸出來一樣,付巧妹團隊通過實驗捕獲釣取了樣本中242個哺乳動物和人類的線粒體DNA。分析顯示,沉積物中的動物古DNA包括犀牛、鬣狗等滅絕動物,與遺址發現的動物骨骼遺存一致,驗證了沉積物DNA分析的可靠性,同時成功獲得了丹尼索瓦人的DNA!
出土樣本的測年是張東菊團隊遇到的又一大難題,同時也是又一項突破。現在考古學研究中,碳十四測年是最常用的測年方法。張東菊研究團隊選擇了14件動物骨骼,在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進行了前處理和碳十四測試,但是遇到了問題,因為碳十四測年是有上限的(43500年),如果碳十四都放射的少到儀器無法檢測到了,年代肯定也沒法測了。結果發現,他們送檢的第4-6層的骨骼已經超出碳十四測年上限。
好在近年興起的單顆粒光釋光測年技術為他們提供了另一條測年途徑。“當石英或長石顆粒被埋藏在環境中,它就像一個計時器一樣開始積累輻射能量。有一天人類把它挖出來,用光去激發它,所釋放出的信號就會告訴我們它已在那里沉寂了多久。”張東菊這樣解釋這種新的測年法。
張東菊團隊將采集的12個光釋光樣品和澳大利亞李波團隊共同開展單顆粒光釋光測年分析,最終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結合碳十四和光釋光測年結果,團隊建立貝葉斯年齡模型,為遺址建立了距今約19-3萬年的可靠年齡框架,將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最早活動歷史又提早了3萬年,也為化石出土于白石崖溶洞、夏河人下頜骨屬于丹尼索瓦人等結論提供了更確鑿的證據。
2020年10月30日,張東菊團隊白石崖溶洞的研究成果在Science(科學)雜志在線發表,再次轟動世界,也回擊了此前對他們的所有質疑。
已知的和未知的
通過發掘和研究,關于夏河人的一些疑問被解開,而有更多的疑問仍然待解。
比如,夏河人使用什么工具?他們吃什么?張東菊團隊在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打制石器,而石器又以刮削器為主,也就是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刀。這又與夏河人的食物有關。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這反映夏河人吃了大量的肉類食物。但是,不同的地層也就是隨著時間變化,出土的動物骨骼又有很大的變化。下部地層也就是早期出土的多是犀牛、野牛、鬣狗等大型動物骨骼,而上部地層出土的多是羚羊、狐貍等小型動物骨骼。這反映出夏河人在十幾萬年的時間內捕獵對象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到底是人類捕獵行為發生了變化,還是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仍是待解之謎。
咱們前文曾經說過EPAS1基因。這是一種人類適應高原高寒缺氧環境的基因,我國青藏高原的居民普遍具有這種基因,而這種基因竟然也存在于丹尼索瓦人的身體里,可是丹尼索瓦洞所在的海拔只有700米,這種基因是怎么來的呢?如今在青藏高原發現夏河丹尼索瓦人之后,問題似乎很容易找到答案:長期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區的夏河人有足夠時間在適應高海拔環境的過程中出現基因突變并富集EPAS1基因。當然,這只是一種合理的猜想,還需要通過更多的發現和更深入的研究來證實。那么問題又來了,我們今天青藏高原居民身上的EPAS1基因與夏河人有關嗎?
夏河人化石同樣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夏河人下頜骨保留有完整的第一、二臼齒,第二臼齒有3個齒根,而第三臼齒先天缺失或未萌發,但留有臼齒后空間。其中, 臼齒第三齒根現象在中國現生人群和美洲土著人群中發生概率超過40%,而在其他非亞洲現代人中發生概率不超過3.5%。這又說明了什么?
當然,還有更多更多的疑問。比如,當我們的祖先現代智人于四萬年前也來到青藏高原,他們和夏河人有沒有相遇?是爆發了血與火的戰爭還是相愛相殺?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們,夏河人是不是“亦有貢獻”?
這一個個疑問既令人困惑又讓人著迷。于是,剛剛從北京領獎歸來,張東菊立馬回到了發掘現場,她要繼續做“高原做題家”。


 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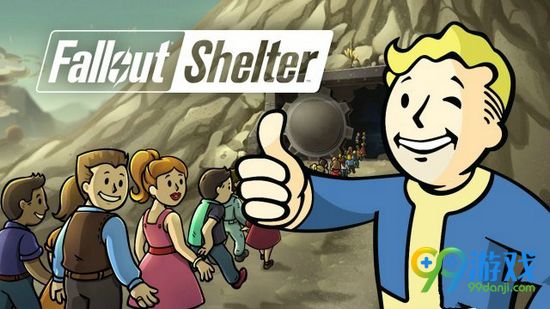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




 熱門資訊
熱門資訊 關注我們
關注我們
